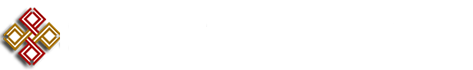老北京四合院的墙,是有表情的。尤其那碎砖墙,用现在的话说,像极了岁月在脸上留下的皱纹——粗糙、斑驳,却透着实在的热乎气儿。
这种墙不挑材料。盖房剩下的半截砖、拆旧屋的残次品,甚至胡同里捡来的碎砖头,都能派上用场。工匠们用掺灰泥——一种石灰与黄土按比例调和的黏合剂,像和面似的把碎砖们"揉"在一起。灰泥抹得宽,卧缝足有寸把厚,立缝却常省略了,墙体因此显得敦实,像穿了厚棉袄的老头儿,看着就暖和。

规矩是有的,但不死板。砌的时候允许"游丁走缝",砖块不必横平竖直对齐,可以错位排列,像孩子搭积木那般随性。可再怎么自由,"通缝不能超三层"是铁律——这是老祖宗传下的智慧,确保墙体不会从里到外裂成一道口子。砖要"整砖拉丁",一律平砌,绝不"陡砌"(立砌),让每块砖都踏踏实实躺着,把力气使在长处。墙砌到两米来高,工匠会往夹空里灌些稀灰浆,让里外皮咬得更紧。若是讲究人家的清水墙,最后一道工序是"勾泥缝":用细竹片把灰缝抹出凹槽,既美观又能挂住灰尘,显出层次。
这墙多用在院墙"上身"——就是底子石以上、檐口以下的那一段。为何不全部用整砖?省钱呗。过去人家过日子,一分钱掰两半花,建房更是能省则省。碎砖墙正好应了这份节俭,把废弃料变成体面的屏障。
可奇妙的是,这"将就"出来的墙,反而最有京味儿。冬天斜阳照上去,厚灰缝的阴影深深浅浅,碎砖的青灰、土黄、赭红虚实相间,像一幅没骨写意画。春雨一打,墙角苔痕上洇开一圈圈水渍,又像老宣纸上的墨晕。孩子们爱在墙根儿底下玩儿,因为灰缝粗,总能抠出点儿灰泥来弹球;猫爱沿着墙头走,爪子踩上去有摩擦力;我姥姥那辈儿人,更是能根据墙上碱渍的形状判断来年雨水大小。
如今,整砖新墙多了,电脑调出的灰缝均匀得像用尺子量过。可每次路过南锣鼓巷或东四那些没拆净的老院子,看见半爿碎砖墙,总忍不住伸手摸一摸——那些粗糙的颗粒、不规则的凸起,还有渗入砖缝的煤烟子味儿,才是四九城真正的底色。墙缝里,仿佛还藏着拉洋车的喘息、煤球炉子的青烟,和那句拖着长音儿的"早——起——喽——"